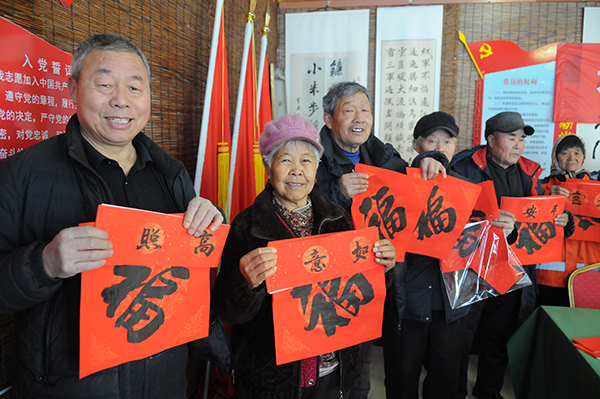从外地回到济南的第二天,就惊闻刘广东去世的噩耗。8月23日上午,参加完告别仪式回到家中,内心五味杂陈,难以平复,与刘总相处的点点滴滴在脑海中一幕幕闪过。
1993年8月的一天,我正在大众日报总编室值班,主任走进来,说“刘总请你到他办公室一趟”(刘广东时任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年轻人一般称他刘总或刘老师)。我当时只是一名普通编辑,还从未单独去过他的办公室,心里忐忑着敲响了门,刘总见到我第一句话是:“小魏,你第一个报名援藏,不错!有什么困难吗?”我一时有些蒙,还没弄清他说的是啥事。定下神来才想起大约三四天前,在部门例会上,主任说上级给了报社一个援藏名额,让大家踊跃报名,我和部门里符合条件的年轻人当时就报了名,这也是报社的传统,但说实话当时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会在众多报名者里中了“头彩”。去西藏是几乎每个年轻人的梦想,但自己当时的确面临着不少困难:大学毕业分到报社,先到菏泽记者站工作了两年,回编辑部刚一年多,又被派到聊城市包村扶贫一年半,这不,刚在总编室安稳了两年,又迎来了严峻考验。更让人放心不下的是,女儿此时才两岁多……
刘总看我犹疑不定的样子,笑着对我说,“知道你家里有困难,不着急,回家好好征求一下家人意见”。
回到家,把援藏的事告诉了爱人,又打电话告诉父母,想不到他们的态度出奇的一致:“既然报了名,组织上又信任,你一定要去!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
援藏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了,父母不放心,专程从老家来看我。我当时住在一幢旧宿舍楼的顶楼6层,没有电梯,一天晚上8点多,突然响起敲门声,开门一看,天哪,竟然是刘广东和时任报社社长的刘学德!他们得知我父母来了,专程登门看望,当时家里没有电话,事前我没得到一点消息,怎么也想不到报社一二把手会在大晚上爬6楼来看望我父母,我激动得手足无措,说话也有些语无伦次。两位领导说了一番勉励安慰的话,便起身告辞。父亲感慨地对我说,“有这么好的领导,你在西藏不好好干,对不起他们啊”。
几天后,刘总又和刘学德等领导在旧办公楼改造的报社招待所为我设宴饯行,吃的是火锅涮羊肉,一个刚满30岁的年轻人,哪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啊!在氤氲的肉香和酒香中,我不知喝了多少酒,也不知说了多少年少轻狂的话……
终于到了出发的时刻,报社送我到机场的车停在办公楼前,我正要登车,突然大众日报摄影记者訾秉会急匆匆地跑过来,说“刘总和其他领导要来为你送行”。不一会儿,刘广东、刘学德、朱宜学、王培文、徐增连、何荣德,还有部门负责人许学芳、徐守礼、张军等等都来了。当时彩色胶卷还比较贵,但訾秉会按相机快门的咔咔声一直没停,一张张合影定格了一个个难忘而珍贵的瞬间。遗憾的是, 这些照片在之后的一次次搬家中竟不知遗落在何处,遍寻无着,但这些难忘的瞬间永远珍藏在了我的心中。
在西藏日报工作,面临的不仅仅是高原环境和饮食的不习惯,更多的是工作压力和想家的孤独。当时西藏还没有普及程控电话,长途电话费也很贵,所以我减压的最好方法就是给家人、朋友和同事写信,援藏两年,算是理解了“家书抵万金”的真正含义。我知道刘总工作繁忙,不想过多打扰他,所以基本上每个季度给他写一封信,简单汇报一下在西藏的工作生活情况,信寄走很快就会收到他的亲笔回信,用现在的新词来说就是“秒回”。后来从同事来信中得知,我给刘总写的信,他几乎都要在报社各种会议上宣读,还摘发在《社讯》上,这让我倍感压力,所以慢慢拉长了写信的间隔。刘总应该是感觉到了什么,在一次来信中问,为什么写信少了,他很想知道我在西藏的情况。我既感动又惭愧,一方面,恢复了原来写信的频率;一方面,更加努力工作,争取不辜负刘总的厚望。
1994年春节前,收到刘总一封厚厚的挂号信,我有些诧异,打开一看,竟是刘总用毛笔在宣纸信笺上写的信,一手漂亮的行书,信的前半部分是鼓励勉慰的话,后半部分是一首七言诗,竟是以在报社招待所为我饯行吃涮羊肉为题写的,全文照录如下:
隆冬火腾涮羊香,众送魏君援西藏
窗外雪飞皑皑地,胸内情激滔滔浪
雅鲁黄河同凯歌,泰山喜马共辉煌
更有环球大同志,定教红旗五洲扬
在信后刘总还附注:我不会作诗,从来没写过,此作只是为了共勉。
捧读三页薄薄的信笺,感慨万千,这是对我个人的关心和勉励,更是对报社所有年轻人的期许和厚望。
两年的援藏生活结束了,我带着疲惫的身体和兴奋的心情回到山东,正逢大众日报社在全国率先进行以运行机制、用人机制、分配机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改革,改革搞得红红火火,我则一边休息,一边在报社办公室做点文字工作,倒也逍遥清闲。不料在改革接近尾声时,我突然被党委任命为报社三名总编辑助理之一,另两位是傅绍万和许衍刚,这两位后来的报社一二把手当时就是两个主要业务部门的主任,绝对的业务骨干,而我只是一名中级职称的普通编辑,何德何能担此重任?这时报社内一些对此不理解的非议声音也慢慢传到我的耳中,一时间感到压力山大,我找到刘总吐苦水,说这是把我放在火上烤啊。刘总笑眯眯地看了我半天,才慢悠悠地说:你以为这是我对你个人的偏爱吗?告诉你,这是党委在树立一个用人标杆,就是不能让甘于吃苦奉献、做出突出成绩的人吃亏,要让他们名利双收。你援藏前按惯例就应该提拔一下,援藏期间宣传孔繁森事迹又做出了突出成绩,所以这次破格提拔没什么问题,你不要有顾虑,大胆工作。我无话可说了,只能按刘总的要求:大胆工作,拼命工作。
正如刘总所说,报社党委借此树立了鲜明的用人导向,不久之后,报社引30岁左右的年轻博士张晓群,因为撰写了多篇有深度、指导性强的调研报告,在报社经营管理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破格提拔为社长助理。一大批年轻人通过公开竞争上岗,走上了处级领导岗位。刘总主导的三项制度改革大获成功,激活了一池春水,极大调动了报社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发展活力持续增强,综合指标在全国名列前茅。尤其是建立起了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意义尤为深远。可以说,集团今天的发展壮大,还在受益于当年的改革成果。
在刘总身边工作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他平时待人和善,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但一旦你工作中出了错,他批评起来也毫不留情。我刚担任总编助理后不久,不知从哪来的传言说我搞特殊,要求拿高奖金云云,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我连这种念头都没有过。这些话也传到了刘总耳中,他找我谈话,我带着情绪辩解起来,他愈发生气,狠狠批了我一通,我没有再说话,但心里感到非常委屈,情绪一度很低落。后来此事得到了澄清,刘总又找我谈话,还是笑眯眯地对我说:受点委屈,被人误解,是年轻人成长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年轻干部要甘于吃苦、吃亏、吃气,心胸要宽阔一点。正是在刘总的言传身教下,我才慢慢学会了如何做人做事,从这个意义上讲,刘总不仅是我的老领导,更是我的恩师。
刘总在年满60岁时退出了报社领导岗位,转任省人大常委。除参加人大的活动外,他又重拾以前的书法爱好,几乎天天沉浸在翰墨书香之中,流连忘返。他的字越写越好,又开始研习中国画,也许是书画同源的缘故吧,他很快入了门,画技精进,创作的作品不仅像我这样的外行看着赏心悦目,许多方家也不吝赞誉之辞。工作之余,我喜欢到刘总画室坐坐,清茶一杯,不谈工作,也不谈报社的人和事,只聊写字画画,他谈兴很浓,我似懂非懂,却也听得津津有味。临别时,刘总照例指着桌上的一卷卷作品说:随便选一幅吧。我拿了两三次,再也不好意思拿了(报社职工向刘总求字画,他来者不拒,而且每每主动送人,许多干部职工,包括工人、司机家里都有他的作品)。但在一次告别时,他没有让我自己选,而是把一个厚厚的大信封递给我,我展开一看,是一副尺寸很大的书法作品,内容竟然是那首以涮羊肉为题的诗(他对诗句做了部分修改),“谢谢”两个字在我嗓子眼转了半天没有说出来,在这份前辈的情意面前,任何感谢的话都显得轻飘飘,我只能以好好做人做事的实际行动回报刘总。
由于长期伏案工作,缺乏锻炼,刘总腰腿都有毛病,还患过两次胰腺炎。我忘了具体时间,应该是2015年的一天早上6点多,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一看是刘总打来的,接通后,话筒中传来他微弱的声音:“我肚子疼得厉害,麻烦你送我到医院。”我马上联系救护车,把他送到千佛山医院,医生诊断后问刘总的爱人刘阿姨什么时候犯的病,刘阿姨说凌晨1点多,医生告诉我们刘总患的是重度急性胰腺炎,当即下了病危通知。在医生的全力抢救下,刘总终于转危为安,在病床边,我问他为什么不早一点打电话给我,他轻轻地说,“大半夜不想麻烦大家”。这次,刘总又是胰腺炎复发,本来病情已稳定,转到了病房,但却因肺部感染,遽然长逝,痛哉!
日本童话《去年的树》里讲了一个美丽而伤感的故事:一棵树被伐倒做成了火柴。最后,火柴也用光了。可是,小女孩告诉苦苦寻找大树的小鸟:“火柴虽然已经用光了,但火柴点燃的火,还在这盏灯里亮着呢。”刘总,您就是这盏灯,燃烧自己照亮年轻人前进的路,用温暖的光引导他们走正道,干实事,做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