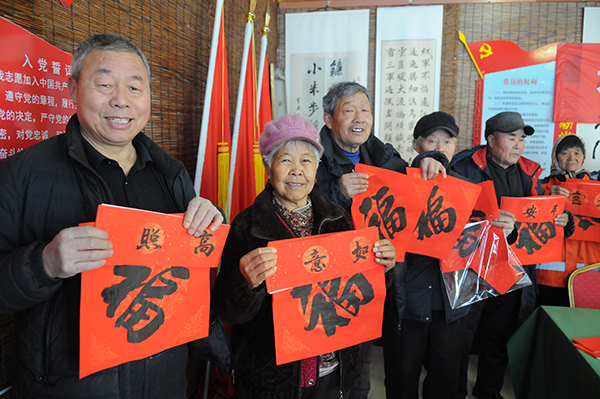当博山老街的青石板被混凝土与沥青彻底覆盖,当八卦琉璃炉内那跃动千年的火光渐次湮灭,一种文明的隐痛便无声弥漫。然而,在历史更迭的断裂处,总有不甘湮灭的灵魂挺身而出。刘连贵与胡国忠——一位七十八岁的老工程师,一位七十九岁的老刑警,以古稀之躯,毅然卸下安享晚年的静好,披上“文化守夜人”的征衣。他们以笔墨为篙,撑起《博山老街》与《博山老城深处》这两艘承载着博山城千年记忆的方舟,在遗忘的洪流中奋力溯洄,将濒临消逝的烟火人间、市井肌理,以实景图画与鲜活口述凝固为永恒的纸上城邦。这绝非仅是对一隅地域风物的温情回眸,更是对深植于血脉的中华文化基因图谱一次惊心动魄的抢救和创造性“钩沉”。
七十八岁的刘连贵,以瘦削肩膀扛起二十余万自费编纂的负担,数字背后是多年积蓄与无私奉公的写照。他身后,二十七位平均年龄六十六岁的编委队伍,共同铸就了这项令人肃然起敬的“银发工程”。这支被岁月染白双鬓的队伍,用最朴素的方式丈量着消逝的街巷:自行车轮碾过旧痕,电动车灯划破暮色,他们无数次经过出租车扬起的尘烟,只为将有限经费悉数浇灌于纸页的生机。九十九岁的朱老太太,记忆如幽谷深泉,她颤巍的话语里流淌着旧日时光的斑斓碎片;而李僖章则以暮年之智融入编委,用摄影镜头捕捉光影残梦,用排版技艺梳理历史经络——普通人,于此成为文化薪火相传的真正主角。
胡国忠老人,这位昔日穿行于罪案迷雾的刑警,将职业赋予的敏锐洞察与严谨考据,倾注于文化废墟的深耕细作。他创造性地践行“文化钩沉学”,使这场抢救绝非简单的史料堆砌,而是在断壁残垣、泛黄影像、耄耋老人的只言片语中,打捞那些被大拆大建碾碎的历史细节:街头小贩的吆喝韵律、老字号商铺门楣上斑驳的鎏金字号、特定节气弥漫街巷的独特气味……他像一位时空侦探,以碎片为线索,在纸上严谨重构起博山老城早已消散的声、光、色、味与烟火人情。这位古稀老人,无数次徒步或骑行,用脚步反复丈量着博山每寸熟悉的陌生土地,他深知自己是博山老街风貌最后的“活体见证者”,其《博山老城深处》二十余万字的厚重,将二十四条街巷、四十多条胡同的魂魄深情汇编。字里行间奔涌着与时间赛跑的焦灼:“我这个年龄是多事之秋,生怕有什么突然变故半途而废,留下终生遗憾。”这份沉甸甸的紧迫感,化作夜灯下伏案的背影,在料理琐碎家务后片刻的宁静中,笔耕不辍,只为在生命烛火燃尽前,为故城立此存照。
刘连贵与胡国忠的实践,如一把钥匙,揭示了文化传承的深层密码:即便承载物质记忆的老街建筑已在推土机轰鸣中化为齑粉,那些由千年工商文明熔铸而成的基因——诚信为本、精益求精、开放包容、敢为人先的精魂,依然如孝妇河水般在博山人的血脉里奔涌不息。他们所做的,正是激活这沉睡的基因密码。通过“钩沉”这一创造性方法,将散落于个体记忆深处、尘封于旧物之中的历史碎片,精心编织成一部完整、可感、可触的文化基因图谱。这为无数同样面临“千城一面”危机、在现代化浪潮中痛失历史容颜的城市与古镇,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民间抢救范式。诚如中国作协主席张宏森先生所洞见:“城市记忆不仅是备忘录和风物志,更是情感史和心灵史。”两位老人与团队抢救的,正是这座城最深沉的情感脉动与集体心灵共振。
当“万物皆可数字化”的浪潮席卷一切,刘连贵、胡国忠们却选择以最古老的工具——饱蘸深情的笔墨,在纸页的方寸之间筑起抵抗遗忘的堡垒。他们以满头银发为冠冕,守护着行将熄灭的文明烛火。这煌煌数十万言的新书,早已超越普通史料汇编的范畴,它是一部用生命书写的、关于“文化自觉”的当代启示录——正的文化传承,绝非在冰冷的钢筋森林中拙劣复刻几个仿古门楼或牌坊;其精髓在于深入历史肌理,激活那些沉睡于族群血脉深处的文明基因,使之在新时代的土壤中重新抽枝散叶、生生不息。
博山老街的青石板虽已深埋,但孝妇河依然流淌。刘连贵、胡国忠们发起的这场民间文化抢救行动,正如孝妇河源头那不息的山泉活水——始于涓滴细流,却因汇聚了无数普通人的赤诚与担当,终将拥有奔涌向前的磅礴力量,在新世纪的文化长河中激荡起不容忽视的回响。这响动,是对过往最深情的告慰,亦是对未来最坚实的奠基。它证明,只要守护记忆的灵魂不散,纵使城池改易,那深入骨髓的城之精魂,便能在代代心手相传中,获得永生。